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同写意
同写意  2022-05-27
2022-05-27
 2396
2396
被热钱追逐的Biotech如今面临“供血”不足的困境——二级市场回调,一级市场融资困难。资本寒冬或许还要很久,是时候抛弃幻想,面对现实。
如何活下去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重中之重,可问题是如何活下去?

5月4日,同写意邀请了三位医药界资深人士——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的创始理事长朱迅、科望医药联合创始人纪晓辉以及药渡创始人李靖等三位博士,齐聚直播间,接受同写意论坛发起人程增江博士的直面提问,共同探讨关于资本寒冬下的Biotech的生存法则。
程增江:Biotech面临资本市场急速下行、集采影响加剧,以及时而爆发的疫情,各位对当前形势有何看法?
纪晓辉:资本市场目前低迷,华尔街几大投行诸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对目前市场都存在很多顾虑。与去年不同,今年除了能源、消费必需品以外,其他行业都在下滑。从资本市场来看,这种萧条不是Biotech才存在,而是整个市场的通性问题, 只是Biotech 更突出。 寒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年年底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低迷持续到年底,明年可能迎来行业的衰退;如果下半年能转好,不会重蹈2008年的覆辙。 市场进入到持久衰退的时期,资金的专注性将会更加凸显。前几年的融资相对顺利,因此很少有Biotech考虑在资金链断链前,能否产出可以让市场为之一振的产品或者数据。但当下,如何对自己公司作出合理的定位和估值,保证公司的现金流,是现实问题。
朱迅:目前的确存有大量可流动的钱,资本是逐利的。中长期资本追逐的目标,是能够在未来的产品市场上,创造出有足够销售额和利润的Biotech。 创新药的红利已接近尾声。60%在纳斯达克上市的Biotech,市值多低于1亿美元,相比之下,科创板却定位未盈利药企需盈利40亿元。拔苗助长的结果是,近半年上市的本土Biotech大部分已经跌破C轮,甚至B轮,但这还未触底。 除了利伐沙班,本土销售占全球销售超过3%的品种很少,自身免疫、罕见病等领域基本占比都是在1%以下,如此小的市场份额,却要求本土Biotech估值比占据全球份额的Biotech都要大,是不切实际的。我历来的观点是,创新药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当下60%的创业都是不合格的。 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活下来。当前在二级市场融资的药企,烧钱速度很快。以同时三地上市的百济为例,手里约有几百亿现金,但仅2021年当年支出就高达160亿元以上,去年16个产品商业化收入约40亿元,除去PD-1和BTK占比75%,剩下14款产品总计销售才仅10亿元左右。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百济的融资能力。 以前我讲投资是从山顶看花朵,现在我要修正这句话,要看花粉。花粉决定了花朵和最后的果实。大乱才能大治,只有淘汰这些non-qualified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才能获得更多机会。但Biotech领域不能大火,大火带来的必然是投机者,这个领域需要一批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和创业者。
李靖:2017年以前,Biotech融资并不是很火爆。现在18A和科创板这两个退出渠道,其实并不理想。资本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丧失了信心,所以很尴尬——产品正好进入II期、III期这些花钱的阶段,但融不到资。一个灵魂拷问,现在做出的产品能不能在未来市场上卖出钱?
朱迅:过往“投一千万、收益一两个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以恒瑞为例,目前它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销售额和销售利润都大幅下降,并不是创新减少,而是创新药弥补不了仿制药的收入缺口。 促进区域的创新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和商业模式,有三个要素:科学、规范、透明、稳定的法规;知识产权保护;适当的医保支付。 未来医药的整体市场一定是孤儿药市场,而中国的Biotech成长还需要8-10年时间,不能通过集采让这些企业在当下死掉。恒瑞十几个创新药卖不过一个中药注射剂,很现实的情况。
纪晓辉:传统的Biotech的退出就三个机制:第一,从18A、科创板或者纳斯达克上市,相对快且容易;第二,并购,国外的Biotech发展40多年来的成功验证的模式,目前国内还不常见;第三,产品进入市场,在市场又可获得真正的利润。 对于中国的创新公司来说,如果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就只剩下两条路,一个是IPO,另外一个是进入到医保系统或者中国内部定价,但前者目前市场状况不好,后者短期赢得利润艰难。 对于Biotech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调整时机,或者挺身进入国际市场,或者瘦身和重新聚焦。很多公司是要通过其它方式比如合作去输血,而不是通过IPO。
李靖:现在新药存在倒挂的问题。4亿是持平点,低于该数额的都在亏损。找不到好的项目,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即便产品已进到II期、III期,如果卖不掉就要迅速停下来。赶热点,只有5%的人是成功的,所以要返璞归真,回到早期,从数据开始梳理。 其实调低企业估值是没有用的。新药要么值钱,要么不值钱。在这个阶段,如果不省钱,烧完钱故事也就结束了,断臂求生才会有一线生机。这就是一个go和no-go的问题,要做就做中国乃至世界的前列产品。
程增江:以PD-1举例,很多公司采取联合治疗来为产品续命,对投资人也好交代。将II期、III期的产品扼杀掉,对绝大多数创新公司来说,都是难以接受,怎么办?
纪晓辉:现在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都在水下,生存和发展必须找到平衡。其实断臂并不是坏选择,只要团队和产品靠谱,时间就成了朋友,企业也会稳步增值,有很多Biotech,因为产品临床效益好,一夜之间估值可以增长数倍。但如果在这之前死掉,就没有了未来。
朱迅:并购是Biotech退出的路径之一,不假,但我个人认为,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做不到的。以纳斯达克为例,其背后有1500-2100亿美元的行业资本,而中国的18A和科创板背后,几乎一分钱没有。其次,谁来并购,为什么并购,这都是重要考量问题。 至于IPO,短期内是条好路,但现在很多未盈利的Biotech已经陷入危机,后续究竟有多少能够坚持下去?同时科创板还有达摩克利斯之剑——三年后必须盈利,而当前很多药企上市即破发。亟需转身。 第一个转身,从成本中心变成利润中心;第二个转身,从Biotech变成Biopharma,但目前很多本土Biotech都处于IND阶段,缺乏商业化经验。过往30年,在美国,由Biotech变成Biopharma的不超过5%,美国尚且如此,中国的难度只会更高。 第三,对大多数公司而言,市值是大公司,但实际上是小公司。按照目前的估值,要想真正达到目前在资本市场显示的市值,还需要顺利发展8-10年。实际上是透支未来,然而不完成上述两个转身,是无法变成实值的大公司。 如果完成不了转身,那就升华。升华是讲未来的出路,但现在出海面临很多挑战,在剧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后续有很多不定数。不光是股民被割韭菜,创业者也被割。 我不否认当下这一波创业的贡献——快速提高了最新最好药的可及性,同时倒逼进口药价格下降。但我们不能将贡献和对行业长久的发展的损害相混淆。
纪晓辉:中国很多Biotech都想变成Biopharma。如果看年报,比如PD-1,未来几年该类药物都是销售支出超过收入,因为市场、占有率、销售人员等都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来。要想盈利,不必大包大揽,可以和已有的产业化机构合作,发挥各自的强项。
程增江:现在很多公司因为找不到好的立项点,就朝新冠药物努力,比如辉瑞、吉利德、盐野义等,李博士怎么看待新冠药物项目的立项?
李靖:中国的新冠立项目前已有二十多。立项和时效有关系,一旦过了时间窗口,东西就没有意义了。科兴的疫苗动手快,中国生物紧随其后已经进入到III期,还有点机会。但后面的还在I期的项目,该断臂就该断,因为赶不上了。当然这里有另外一个逻辑,即建立的平台可用于之后其他冠状病毒,但这又回到discovery。
做新的东西,要知道三件事:世界在干什么;全中国在干什么;自己的人财物。 制药行业如同下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九段选手,除却天分也要扎实基本训练。很多企业都基础不稳,连基本的guideline都不明白。举个例子,做小分子药物,熔点需要大于120℃,否则压片时晶型会改变,后续就需要额外多投入1千万美元来补救。所以说打好基础很重要。
程增江:大家都在赛跑。等你知觉,已经晚了三秋,而此刻还要停下来学习基本功,火的窗口就错过了。这个时候需要多拉快跑,guideline不清楚,就赶紧补救,资本市场的窗口不定开几年。
李靖:其实从Biotech到Biopharma有几个指标衡量。 首先,是2+1,即国家医保、省级医保和近月的会议谈判必须得经历。过了之后,开始组建团队,起步400个人,但最好是1000人,分散到全国,拢共需要准备10亿元投入。其次,需要测算单产和人数能否盈利。 这些商业化步骤一定要思考清楚,否则到最后一定是一地鸡毛。
朱迅:医保和定价是两座大山,尤其是定价,当下更严苛。对于已经有多个产品上市的公司而言,情况好一点,但是对只有一两个产品上市的公司而言,想要打通各个环节,差不多得十年,十年之后,仿制药一大堆,已经没机会了。 对患者和国家来说,没什么坏处,你愿意做先驱,成功失败与否尽管去做。但是对资本而言不是好事情, 前期的很多投资都不赚钱,很多资本就会离开这个行业。
程增江:Biotech现在都想方设法拿地,总体来讲,拿地对于Biotech是一个利还是弊?
朱迅:在当下情况,拿地是以进为退,因为现在的Biotech都没有任何资产,我个人认为账面现金不算资产,因为花得太快。 地不一样,至少地可以向银行贷款和抵押,而且还有增值空间。但是这些砖头瓦块,不会让你公司在资本市场增加一分市值。在当下,对于这些Biotech来说,最好是可以将现金转换为能够维持公司未来价值和增长的东西。 新药研发,从临床前到IND这段距离是死亡峡谷,同时也是机会峡谷。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医药领域,仍有巨大的需求。如果现在能沉下心,布局一些早期不太贵的产品,未来3-5年后,当绝大部分企业缺品种时,真正有价值的品种就会成为市场的硬货。 实际上,创新药研发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多的运气性,击鼓传花也好,庞氏骗局也好,但只要你能够做出几个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就可以脱颖而出。mRNA疫苗是个好例子,多年发展中死掉了好多相关企业,但恰逢新冠疫情,又迎来新机遇。
纪晓辉:大家面临不同的情况。拿地可以是明确的战略投资,如果产品商业化的路径明确,比如PD-1的领跑企业,我认为他们需要拿地。拿地能够保证药品生产成本的可控性, 创造价格优势。与CDMO合作生产,则会使盈利滞后。 对许多聚焦全新创新药的Biotech来说,如果药品上市的时间难以完全确定,拿地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造成投资和回报的时间错位。一个生物公司能否辉煌,毕竟主要依据其管线的能力,而不是房地产运作。
朱迅:我个人预测,在未来的3-8年之间,在Biosimilar领域,生产会出现Biotech的“富士康”。现在拿地建生产线,利用率实际上很低,后期要想引进最尖端的人才、工艺,成本愈加高昂。 以重组蛋白类发酵来说,很多工厂自己生产的每克蛋白在80-120美元,而好的一些CDMO可以将费用降到60-80美元,未来3-5年或会降到40美元,在7-8年之后会降到10美元。建厂的重置费用很高,建厂之后又不饱和,属于浪费。
程增江:我们看到很多药企都在从抗体转到CGT和mRNA赛道上,抗体药的红利期是否已经结束?
纪晓辉:抗体药物还处于发展壮大阶段, 前景可观。近几年在FDA的批准的药品中,治疗型抗体占了很大一部分。 双抗的应用是新的趋势,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作为非自然的结构分子,它们对生物学机理的协同作用需求很高,但已有成功的商业验证,未来可期。 CGT已经有了科学和商业验证,最大的问题是医保和价格,除非商业医保能进来,不然仅从CGT盈利很难。因为CGT个体化,费用昂贵,接受人群数量有限。传奇在这方面的竞争力来自国际市场,它的产品有足够的商宝支付,也有潜力进入美国医保,因此利润空间大。
李靖:做药得拿定决心,生物医药不是快消品,一旦动手,十年是不能变的。选择的赛道不能热,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没人没钱,一旦热了,就成了比人比钱,胜出的一定是人多钱多的企业。 十年前我创办第一家宠物药的研发公司,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因为大家觉得丢人,不想做宠物药,有近8年的时间,是无人过问的。去年开始火起来了,国药、复星等大公司都涉猎,如果我现在进入市场,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创业者才是最大的韭菜。创业者的融资是背债务的,因此更得要冷静和客观判断情况,先给自己几年冷板凳坐。
朱迅:创业者会发现,股份是很难出让兑现。很多上市公司已经经历一段纸面富贵的时光,现在市值大幅度缩水。股份如果有价值是钱,如果没有价值,那就只是数据,甚至负债。这个过程中,职业经理人获得最大收益,但创业者实际被绑在里头。
李靖:传奇有好的立项,但没有J&J是成不了的。其实我们有好多企业,有好的想法,但没有资源、钱和人,实现不了,后面又有时间追着。传奇的项目如果说再拖三年,以他们自己融钱的速度,不靠J&J,就是另一个故事。 速度和智慧,缺一不可。
纪晓辉:一切最终会回归到起点。传奇发展的背后是坚实的科学,以及难得的机遇,但从起点来讲,传奇定位明确,竞争点独特,辅以产品优秀。这个起点对Biotech来讲不易,也未必很难,关键是创始人当初能不能秉持科学,有没有勇气去尝试突破。 刚才李博说要看世界在做什么,以往我看世界,是为了跟上,因为安全。但早期的安全是后期的危险。在今天,平衡更加重要,赛道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李靖:有人有钱比速度,没人没钱比智慧,从古到今都这个道理。但对于大部分创业者,都是没人没钱,胜出不是靠蛮力比拼,而是凭智慧。纪博士刚才问,既然抄为何局限于中国市场?只能说,不是每个人有传奇的智慧的。 智慧大旗不倒。想要活下去就要紧缩银根,转向花钱少但品质好的discovery。
朱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下中国的卫生支出处于低值,十年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从4.85%涨到6.85%,一直保持稳健的增长。未来会有更大的需求增长。 另外,目前现在全球销售额最好的药物,其中70%是近十年出现的。未来的十年,肯定会有一大批新药来替代当下这些药物,新药来自哪里?一定是临床前研究。 未来的创业机会更多。经过这一轮的回归医药创新,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创业和投资者专业程度更高。在医疗需求增长的未来,我认为药品和器械是重中之重。而在当下,得先剩下来,活下去,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否则会永远成为这个领域的分母。知史鉴今,从过往的数据剖析规律。 但仅此是不够的,距离创业成功仍有很大距离。首先要将这些不同层面的数据变成情报,其次,需要有行业经验支撑形成判断,最后再形成最后的决策。新药研发是高度不确定事件,以上三个环节越坚挺,就越靠近成功。 逻辑已经改变,创业者和投资者应当用新的逻辑来考虑、迎接未来创新药研发的新格局。
纪晓辉: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无论是金子还是银子,一定要走向国际,去挑战全球市场。从未来看现在,这是中国Biotech当下对定位和态势应有的思考和必然的趋势。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识林
识林  2025-07-03
2025-07-03
 12
12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
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  2025-07-03
2025-07-03
 1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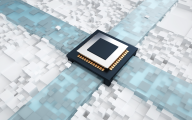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医药投资部落
医药投资部落  2025-07-03
2025-07-03
 14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