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PharmLink
PharmLink  2025-05-07
2025-05-07
 569
569
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动荡、贸易政策变化、人才流动与监管改革等多重因素交织,全球制药行业的产业布局正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欧洲老牌药企正在面临来自美国关税、亚洲国家加码吸引投资,以及欧洲内部政策激进改革等多重夹击。
在此背景下,英国–瑞典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的一则表态引发业界关注。

阿斯利康近日公开告称,欧盟的药品定价和监管政策削弱了欧洲的创新竞争力,甚至威胁到本土医药供应链的稳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帕斯卡·索里奥(Pascal
Soriot)指出,欧洲在创新药物上的投入占GDP比重远低于美国,导致欧洲在吸引研发与生产投资方面落后。有媒体报道,阿斯利康正计划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布局,考虑将“部分药品生产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规避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征收的进口关税。阿斯利康已经在美国拥有11个生产基地,现阶段也在计划“对面向美国市场的药品生产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显现出其对欧洲政策环境日益不满的立场。

阿斯利康表态与背景
阿斯利康近期的表态并非孤例。
在4月23日发表的一封致英国《金融时报》的公开信中,诺华(Novartis)和赛诺菲(Sanofi)两家药企首席执行官也呼吁欧盟放宽药品价格管控,认为价格限制“抑制创新,使欧洲缺乏吸引力”。

对此,阿斯利康CEO
索里奥表态称,类似于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欧洲现在也必须加大对医药创新的投入和支出,以维护“健康主权”。此前,阿斯利康在英国投资的5.6亿英镑疫苗工厂项目就因英国政府补贴减少而取消,传闻或将转移至美国;同时公司已经宣布将投资35亿美元扩大美国生产产能。
阿斯利康中国市场方面也在持续发力:2025年3月宣布将在北京建设25亿美元的研发中心,并与多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达成合作,体现了其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这一系列动向凸显了阿斯利康利用全球资源平衡其生产布局的决心。

欧盟药政改革:政策内容与争议
当前,欧盟正推进《药品立法改革》(欧盟医药法修订)。
2023年4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综合性改革方案,意图解决药品短缺、改善跨国可及性,并鼓励创新。其中核心措施包括缩短药品上市前审批流程、加速仿制药上市;对现行的“8+2+1”年保护期体系进行调整。据内部文件和报道,提案中“将现有药品享有的10年独占销售期削减两年”,并仅当新药在两年内在欧盟全境上市后,才返还削减的保护年限。同时,临床试验数据保护期也拟由8年缩短至6年。欧盟方面认为,新规将促使药企将创新成果更快推向欧盟各国市场,从而缩小新药在成员国内部准入时间差距,并通过药品价格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研发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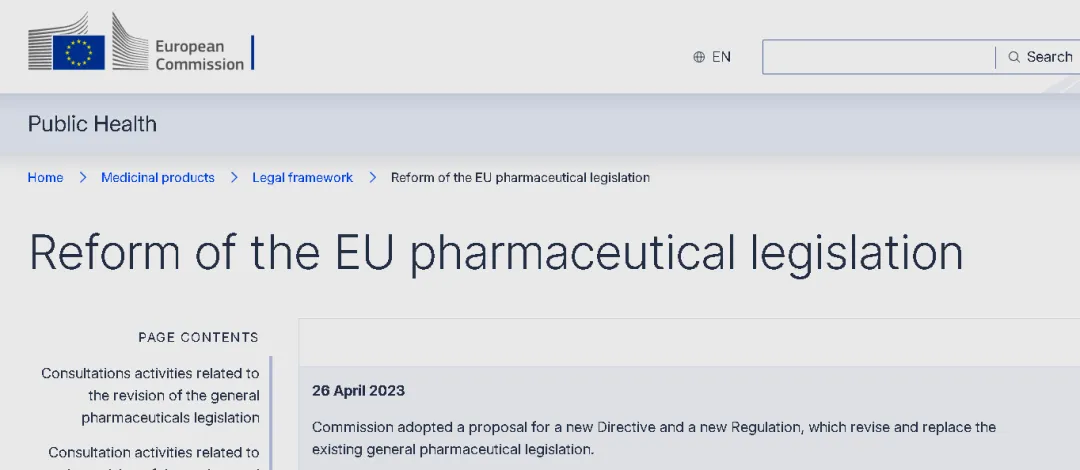
然而,制药业界对此存在诸多质疑。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Stefan
Woxström曾直言,缩短数据保护期“将降低研发投资并扼杀创新”,因为这会显著缩短企业回收成本的时间窗口。业内普遍认为,在当前欧盟医保价格低、审批周期长的环境下,再削弱知识产权保护只会促使企业把研发和生产转向更高回报的市场。欧洲制药工业和协会联合会(EFPIA)警告称,新规若实施,到2040年欧洲在全球药物研发投资的份额可能减少三分之一,每年将流失约21亿欧元研发投入。并且提案中的“全欧上市”要求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因为实际上药品获批后往往仍要经历各国单独定价与报销审批。
行业还指出,新规将增加额外成本,如新修订的城市污水处理指令要求制药企业为废水中微污染物治理支付费用。多家药企在致欧盟的公开信中呼吁简化法规,例如目前在欧洲进行药物临床试验通常必须跨国执行,他们希望减少此类多国审批负担。总之,欧盟拟议的改革在提高可及性、强化公平方面虽有政策考量,但若执行过猛,可能导致欧洲失去“创新友好”环境,令企业投资信心受挫。
行业动向:全球投资与市场担忧
不仅阿斯利康在重新布局,其它跨国药企也纷纷宣布加大美国或中国投资,这是除欧洲外的两大经济体。
2025年1月发布的财报电话会议上,礼来(Eli Lilly)表示将在未来五年内在美国新建工厂项目投资270亿美元;强生(J&J)也宣布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投资增长25%,总额超过550亿美元。5月的媒体报道指出,默克(Merck & Co.)将在特拉华州投资10亿美元建新药厂,以扩大美国本土生产能力。礼来、强生和默克都明确表示,此举旨在应对可能的美国关税威胁,并减少供应链风险。

与此同时,制药巨头纷纷加大亚洲市场投入:阿斯利康在中国持续投资,不仅升级青岛无锡生产基地,还计划在北京建立大型研发中心;辉瑞(Pfizer)也在华扩张生产线和研发据点。可以看出,大环境推动下,美中等地区通过税收、采购承诺等政策,吸引了大量医药产业资本,而欧洲市场则因为严格的价格管控与高成本受到企业诟病。多家药企如辉瑞、礼来、阿斯利康等在致欧盟官员的信中坦言,欧洲与美国相比定价体系存在“双重劣势”,美国药价普遍几乎是欧洲某些国家的两倍,这也进一步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和投资配置。
对欧洲医药产业链的影响
阿斯利康的表态揭示了欧洲制药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欧盟自身政策文件也强调,新立法旨在“确保关键药品供应安全”。若大批核心企业将生产迁出或缩减欧洲产能,欧洲国内供应链的稳定性将难以保障,药品短缺风险上升。阿斯利康高层甚至警告说,如果欧洲不加大创新支持,“生产和研发岗位将随着时间推移转移到美国”。这一点在数据上已有体现:据行业报告,欧洲制药业2023年研发投入约500亿欧元,直接雇佣约90万人,并带动了约270万条上下游就业机会。这些人员与投资的流失将是沉重打击。

此外,药品研发、临床和监管等专业人才的全球流动性增加,也意味着欧洲创新生态面临倒退风险。以默克新建美国工厂为例,该项目预计可提供500个以上的全职岗位;反观欧洲相应岗位可能减少。而目前欧洲在全球药品销售中的份额也在逐渐下滑,仅占新药市场的不到25%。如果进一步失去生产和研发能力,欧洲即便已有欧洲医药联盟等战略倡议,也将更加依赖海外市场和供应,无法有效实现卫生自主。
结语
阿斯利康及其他制药巨头的动向表明,严苛的定价与监管环境正在危及欧洲医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短期来看,欧洲需要审慎评估新法规对产业造成的负面冲击,而长期则需要通过灵活的市场激励、研发投入和供应链政策来重建“健康主权”。政策制定者若能在平衡可及性与创新激励之间找到新平衡,或可避免生产业空心化。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药时代
药时代  2025-11-07
2025-11-07
 13
13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瞪羚社
瞪羚社  2025-11-07
2025-11-07
 1
1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深蓝观
深蓝观  2025-11-07
2025-11-07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