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药创新
药创新  2025-11-04
2025-11-04
 139
139
当前最难治的三种消化道肿瘤(胰腺癌、胆道肿瘤、肝癌),未来如何破局?
近年来我国肿瘤防治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临床诊疗技术的革新到本土药物研发水平全面提升,中国在临床肿瘤学领域的进步国际瞩目,可喜可贺。
然而,正如曹雪涛院士在第十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的主旨报告中指出的:我国在抗肿瘤药物的源头创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关研究成果向临床价值转化的过程,亦面临多重的挑战。
就消化道肿瘤而言,我国是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的高发国家,存在着巨大而迫切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10月26-27日,在上述大会上,国际著名的消化道肿瘤诊治与临床试验专家、中国药科大学附属南京天印山医院的秦叔逵教授接受采访,针对国内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中国有关临床研究的全球地位、消化道肿瘤研究未来突破口等关键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深刻的见解。
秦教授特别向“药创新”指出,对于肺癌、乳腺癌等全球高发的癌症,已经达到了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已有的药物极为丰富,后续新药多为“锦上添花”。但是,对于胰腺癌、胆道肿瘤和肝癌,诊疗困难,新药研发面临较大的挑战,疗效亟待提升,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雪中送炭”的机会,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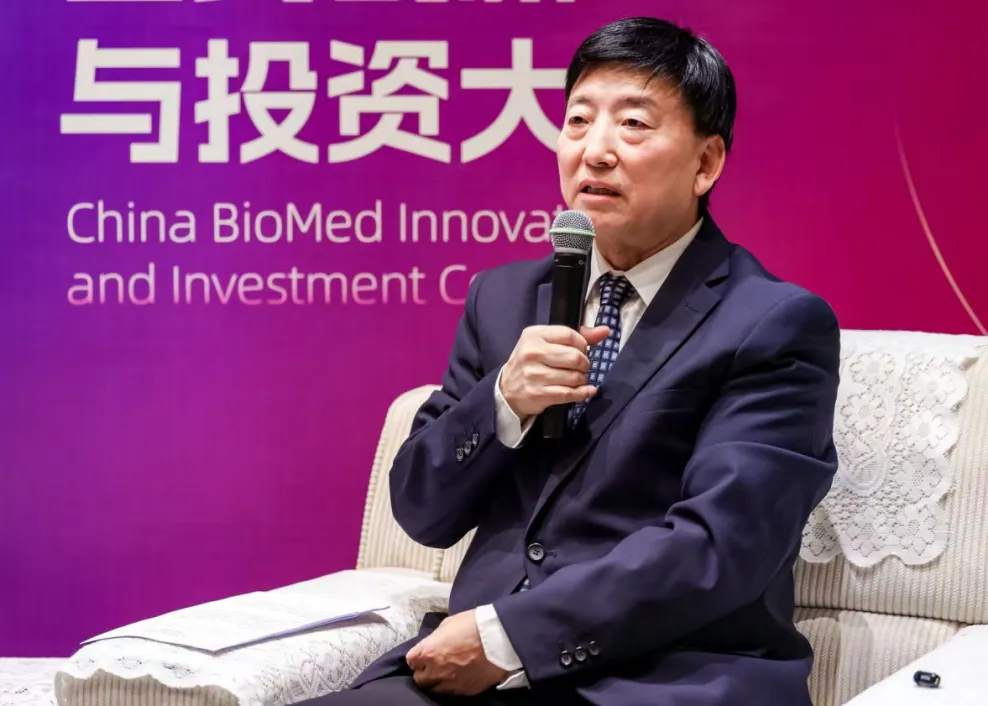
秦叔逵教授接受采访
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肿瘤新药研究的全球地位?国内药企在肿瘤药物研发上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秦叔逵教授:作为肿瘤科临床医生,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近十年我国在肿瘤诊断治疗上的巨大进步;尤其是2015年党和政府提出“健康中国”宏伟战略布署;紧接着2016年公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后,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和科技部以及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为肿瘤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治。
与以前相比,目前中国肿瘤临床诊疗和研究的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2年2月,亚洲临床肿瘤学联盟(FACO)成立之时,我们许多时候都在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如何做肿瘤临床研究。如今,我们在多个肿瘤领域的临床研究水平业已达到了亚洲领先水平,甚至跻身于世界前沿。比如,在刚刚结束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2025年度大会上,近20%的重磅研究成果来自中国,其中樊嘉院士和周俭教授团队公布了“双艾方案靶免联合用于肝癌围术期治疗的3期临床试验”的主要数据,获得预期的阳性结局,主论文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主刊上,引起全球肿瘤学者的轰动,好评如潮。
不过,我们也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上述曹院士提醒的差距。国内研发的许多肿瘤药物属于Fast-follow产品,真正属于First-in-class的原创药物还比较少。虽然有许多肿瘤管线的新药出海成功,海外授权交易合同金额很可观,已超千亿美元,但是多为ADC、双抗等药物类型,其核心技术平台仍然源于国外,而国内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平台罕见,几近空白。
这种情况背后的问题可能在于产学研医的融合不足。通常对于肿瘤药物新靶点、新机制的发现,应该更多地依赖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而非药企或临床医生。未来,本土医药企业需要特别加强与上述科研机构的合作,结合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寻求突破,切实从Fast-follow向First-in-class转型,才能真正实现源头创新。
作为许多项临床研究的Leading PI,您是否感受到中国在全球临床研究中地位的变化?例如,过去中国通常在全球III期临床研究时才加入,现在会参与I期临床和更早期的研究。
秦叔逵教授:中国临床研究的能力、水平和全球地位,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
2016年前后,我与国内多位知名临床研究PI一起与某跨国药企的高管团队交流。当时我提出了三个问题:贵公司口口声声讲高度重视中国,与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可是迄今却只在中国开展过小型的桥接试验,其目的是新药的上市销售,有没有在中国开展过早期和关键性临床试验?其次,对于中国高发且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肝癌、食道癌、胃癌及鼻咽癌,是否开展过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第三,除了有时邀请中国专家学者参加“跑龙套”之外,有没有真正看重和协助我们牵头组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对于这些问题,对方的回答是三个“No”。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汗颜。
后来,这家跨国药企确实逐步增加了对中国高发肿瘤的临床研究的投入,特别是针对肝癌的研究,邀请中国专家参加和担任国际多中心的Leading PI,推动了我国和全球临床研究的进步,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
今天,中国参与的国际临床研究数量逐年增加,跨国药企在新药研发立项时也会更多地邀请中国专家参与,一些跨国药企还会与中国专家共同探讨新靶点药物的开发。早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我们只能分享本土单中心的数据,而现在可以分享更多国际临床研究的数据和经验。这些既体现了跨国药企对中国医学界和市场的进一步重视,也印证了中国临床研究者在全球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对于创新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转化,国内还存在哪些瓶颈?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秦叔逵教授:临床研究成果的转化落地,需要多部门协同和全链条配合跟进,包括药企、医院、科研院所、卫健委、药监局、医保局以及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心协力,在支付端的协同和衔接。
在药企层面,当前的研发多为一窝蜂上马,聚焦于Fast-follow、Me-better类药物,集中在HER2、TROP2少数靶点,赛道极其拥挤,内卷严重,未来需要差异化研发,从追求数量转向提升质量,向First-in-class突破。
医疗机构方面,不同等级的医院也应该差异化发展,根据自身条件分工参与到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中,比如基层医院应该侧重于诊疗与新技术的应用,而北上广和南京等中心城市的三甲大医院则需要强化产学研合作。
此外,部分医院在开展临床研究时,自己的医生干活少,过于依赖临床研究协调员(CRC),观察病人不细致,书写病历不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床试验的质量。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应该进一步改进,借助人工智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确保临床研究的科学、真实和可靠。
国内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上还有哪些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未来5-10年,哪些治疗技术有望在消化道肿瘤领域取得突破?
秦叔逵教授:在全身所有肿瘤中,肺癌、乳腺癌和消化系统肿瘤加起来,占比高达85%;而消化系统肿瘤中,胰腺癌、胆道肿瘤和肝癌是目前常见且最难治的三个瘤种,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极为显著和迫切。
首先是“癌中之王”胰腺癌,目前仍然是以化疗为主,靶向治疗选择少,免疫治疗效果不佳。不过,胰腺癌的分子分型已经较为清晰,KRAS突变是驱动基因。因此针对KRAS抑制剂,国内外多家药企正在积极布局;同时联合治疗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有望进一步提升对胰腺癌的疗效。
CLDN18.2也是胰腺癌的重要靶点。业内正在开发靶向CLDN18.2的ADC、双抗及CAR-T等,尽管遇到一些波折,仍然有望为胰腺癌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其次是胆道肿瘤,包括肝内胆管癌、肝门胆管癌、肝外胆管癌以及胆囊癌等。过去胆道肿瘤也是主要依赖化疗,疗效不佳,之后虽有HER2抑制剂、FGFR抑制剂、IDH抑制剂等靶向药,主要用于二线治疗,单药应用效果有限。近年来,免疫治疗的进步为胆道肿瘤带来了新的机遇。刚刚结束的2025ESMO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团队报告的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联合GC化疗(靶免化方案)的IIT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针对肝细胞癌,尽管我国已经批准二十款治疗肝癌的药物上市,可是仍然面临两大关键性难题:一是尚未找到一个明确的驱动基因,缺乏公认成熟的分子分型,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难以突破;二是肝癌患者的五年总体生存率不足15%,远低于乳腺癌的90%和肺癌的30%-40%,临床疗效仍需全力提升。
胃癌和食管癌的治疗进步较为明显。例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针对CLDN18.2的CAR-T治疗研究,不仅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上做报告,还发表于国际顶刊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实力。
除了上述提到的分子靶向治疗、ADC、双抗、CAR-T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外,肿瘤疫苗、溶瘤病毒等新型治疗也有望取得进展。
因此,肺癌、乳腺癌已有较为丰富的许多精准治疗药物,后续开发的药物可能多为“锦上添花”,而消化系统肿瘤治疗药物有限,仍有大量的“雪中送炭”的创新空间,未来将是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和重要突破口,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先恐后,做出贡献。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新药猎人笔记
新药猎人笔记  2025-11-24
2025-11-24
 43
43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细胞基因治疗前沿
细胞基因治疗前沿  2025-11-24
2025-11-24
 46
46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Medaverse
Medaverse  2025-11-24
2025-11-24
 46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