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E药经理人
E药经理人  2021-06-29
2021-06-29
 2346
2346
近年来,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都在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转变,临床试验的诸多实践也都为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随着中国临床药物试验机构正式进入备案制时代。临床试验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试验承接能力也产生了质的飞跃。
百舸争流的时代大潮下,如何通过职业化的运作,数字化的技术,在借鉴海外临床试验机构的模式之下,走出中国临床试验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成为医药同行关注的焦点。
在2021中国DIA年会的分会场上,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助理李宁,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全球肿瘤研发高级副总裁何静,泰格医药临床运营部总监吴宝林等专家和企业代表也分享了他们在临床试验实践中的心得。
01 临床试验的“职业化探索”
2015年开始,在严格的质量管控、科学的评判体系和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中国的临床试验迎来了黄金时代。
随着临床研究的分工逐步明细,岗位逐步健全,对临床从业者的职业化要求也提出了要求。
与会嘉宾认为,临床研究所涉及的一系列链条中,卡脖子的问题一是在于行政审批,二是临床试验。而如今行业不断的呼吁加速度,也提倡加速度和要求加速度,那面对这两个卡脖子的环节,行业可以有四种应对方式,这甚至可以从仿生学角度模仿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
一是“避开,用新生血管代替”,即去中心化,比如如今的“DCT”正如火如荼;二是“绕过,搭出新的通路”即创建研究型医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是“打通,溶栓支架再通”,即建立职业化中心,主动迎合时代需求;四是“等待,减少工作符合”,即量力而行,用原有模式尽微薄之力。
“如今都提倡中心化,全面对接临床研究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什么是中心化?中心化的实质就是专业化,而专业化的方向是职业化。想做一个中心化的临床试验机构,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如果没有人,跨部门运行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测算过,如果一个临床机构少于12人,是无法支撑的。”与会嘉宾认为。
在他们看来,临床研究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对专业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临床行业的发展需要专业的学术精神和职业的使命责任,这等于是在临床诊疗的基础上,又上了一步。你不光要知道一般性的医学知识,还要了解临床的全流程,了解规范,知道标准治疗如何做,你的知识也一定要与时俱进。而除了学术之外,你还要有职业精神,也就是一种使命感,考量的范围要扩大到自己的未来,甚至是行业的发展。”
而如果提到职业化,就不能不兼顾架构的设计和经营的门槛。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临床研究是一个繁杂的工程,在机构内部牵扯极多,所以在架构上要关注“手表中的每一个齿轮”,也要充分考虑利益的分配,不能一直“用爱发电”。而曾经有专家测算,临床试验机构想要实现正循环的发展,在经营上需要达到一个体量,这要求机构一年的收入大概要在3000万元到5000万元之上。
“职业化的概念在政策上已经给予了明确的认可。在42号文里就提出,鼓励医疗机构设立专职部门,配备职业化的临床研究的病房试验研究。临床研究是一项专业的学科,也是一项专门的科学,值得我们以职业化的精神去探索。”与会嘉宾强调。
02 创新临床机构建设的四步棋
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临床试验机构正式实行备案制起, 中国临床试验机构能力稳步提高, 全国备案临床试验机构总数达到1006家。2020年,在临床试验登记开展的试脸机构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67个试验再次占据榜首, 2019年排名第七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上升至第二名。
但仍具挑战的是,2020年CDE登记开展的临床试验机构还不足全国备案临床试验机构的40%,试验机构资格认定门槛降低,但对试验机构和参与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 “宽进严出”的监管理念。
在与会嘉宾看来,中国临床研究机构建设还需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起高水平的临床研究中心和试验运行体系,二是如何提升监管审批效率和质量,三是如何增强医院和研突者团队对从事临床试验的动力,四是如何应对临床研究经费管理和利益分配上的挑战。
在美国,一般由国家癌症研究所推动国家癌症研究计划的执行,采用多元化的运作模式,创建支持平台,整合资激,加强各研究中心合作。
“这对中国临床研究体系设计的借鉴意义在于,应将医药创新和临床研究水平的提升定位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协同多部委联合推进。”与会嘉宾表示。
此外,他们还认为,在体系设计上,应该鼓励建立多种模式共存的临床研究中心体系,并推动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学术性临床研究组织,引领临床研究水平提升。
“从激励机制的设计上,在医院等级评定和绩效考核方法中也应该增加临床研究相关指标和比重,单独设置并考核研究相关人员和床位编制,提供足够的资源保障。还应该探索设立研究型医生职业发展路径,让医生有动力、有资源和有空间开展临床研究。”与会嘉宾称。
在临床研究中心试验启动阶段,如果更快速地通过审批也成为参会者关注的焦点。
与会嘉宾对照了海外临床试验的审批周期,以及美国癌症中心MSK的运作模式,对中国临床研究机构如何提高整体审批效率给出了建议。“主要有两方面的效率可以提升,一是监督审批的效率,二是伦理审批的效率。”
在监督审批上,与会嘉宾建议,可以考虑让临床试验申请审查、伦理审查和遗传办审查平行进行。
“具体的环节上,可以落实协作审查机制,尝试建立中心/区域伦理审查制度,提高多中心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效率,通过平行审查提高当前遗隹办审批效率,提升机构合同商议和审批效率。”
而在伦理审批上,嘉宾则建议,应该鼓励多样化的伦理委员会类型,改革伦理审查的监管体系,保证伦理审查的质量和合规。
“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提升伦理委员会能力,比如建立伦理评审专家的职业认证机制及培训机制;鼓励参与国际国内认证,提高中国临床研究受试者保护体系建设的整体水平和宙查能力;还可以探讨在医院评级标准中,加入对机构伦理委员会能力的考评。”
而关于如何对中国的临床研究中心进行管理,与会嘉宾建议,,临床试验应以研究者为核心,中心承担服务和协助研究者的角色,可具备多样化的服务模式。既可专门服务一家医院内的医生,比如隶属医院的部门,也可以成为独立的第三方,面向各医院医生提供集中化, 平台化的服务,具备协调多中心,推动高水平临床试验的能力。
“除此之外,也应探索在临床试验中心和研究者团队中建立合理、透明、标准的利益分配机制。还应通过监管核查、建立惩戒机制、鼓励第三方GCP认证和长期能力理念提升等方式,确保临床试验数据质量和受试者保护。”与会嘉宾称。
03 多中心临床下,沟通成关键
临床试验作为药物研发的关键环节,因庞杂的体系,极其依赖申办单位与临床研究单位的配合与有效沟通。
在此过程中,如何让申办单位与研究单位的沟通桥梁更加通畅,是提升临床试验效率的关键。
有机构为此进行过调研,发现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对沟通障碍的反馈主要集中在机构、研究者、伦理审查和护理等参与方,而程序性和实操性的问题则是主要障碍。
对此,与会嘉宾分析称,如今临床试验在多中心进行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多中心的比率已从2016年的88.5%提升到2020年的接近98%。在此过程中,试验设计的复杂性,流程的复杂化都增加了沟通的难度和技巧需求。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前置立项和伦理;也可以利用公开媒介发布办事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人员分工,做到接洽专人专事,同时兼顾交接的连贯性;利用数字化和远程化优势提高速度和效率;但在提速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提质,这是解决我们沟通障碍的关键。”与会嘉宾建议。
此外,他们还提出,在每个阶段都做出充分的准备和应对方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沟通的开放性很重要,临床CRO也会面临知识点的盲区,但通过积极的学习和与参与者的交流,可以缩小盲区,扩大共识。比如中国企业想在欧盟开展临床,以前大家接触都不多,但通过其他同仁,包括CRO一起提供支持,一样可以推动项目往前走。而对于目标,我们有时可以将它翻译成一个可执行的方案,再拆解成最小化的行动单元,这样就能收到到非常具体的反馈,并能得到现实的执行。”
有嘉宾以冷链物流举例,在业内看来,冷链物流是一个很小的模块,涉及的管理计划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一个MRCT的项目在国外的合作中,冷链物流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国内有顺丰可能做得就很好了,但我们在巴基斯坦开展临床项目时,发现冷链物流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它没有合规的包装箱,没有相应的熔点的温度,我们2~8度的疫苗运输,它包装耗材里面熔点的温度应该是5摄氏度左右,而当地并没有5摄氏度熔体的相应的冰包,只有0摄氏度的,那么如何在0摄氏度的情况下去保证我疫苗2~8度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前期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包括在你认知之外的事情,提前去做完整合规性的核查,包括帮他去组建相应的温度的整个流程,从国内进口相应的耗材甚至物流冷链的所有的设备,去重新组织这一链条,让当地有能力去做合规的运输。这一系列流程都需要非常好的沟通。”
有嘉宾形容临床试验项目的各方就像一个剧组,“研发人员出剧本,CRO是导演,PI是演员,申办方是投资方,各方要有机协作。”
“具体来说,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需要提升科研能力,包括高水平论文发表,以及创新药物研发和专利申请。而在资金上,研究中心也应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做到资金独立核算,先收后支,专人转账,专款专用,来源和支出正规且可溯源,可提供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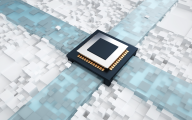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医药观澜
医药观澜  2025-05-23
2025-05-23
 34
34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与制药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与制药  2025-05-23
2025-05-23
 30
30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空之客
空之客  2025-05-23
2025-05-23
 31
31